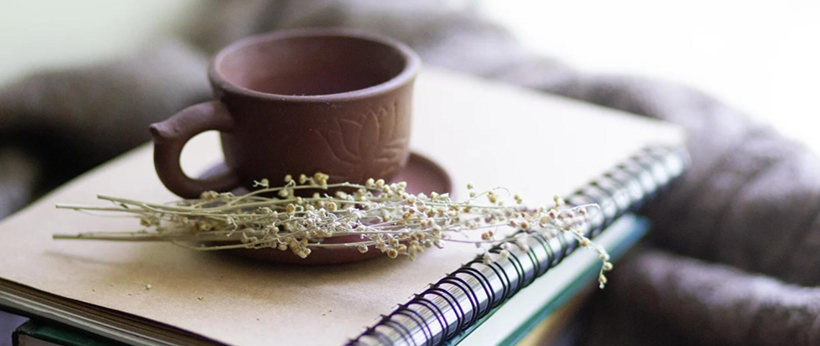"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新纪元'下的驱动与发展机制"
一、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后续发展期”建设的内涵解析
“后续发展期”指的是某一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结束后,其影响力持续存在并推动相关领域进入新旧交替、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此语境下,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的“后续发展期”建设,是指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颁发为重要标志,关注这些成果在后续阶段中的推广效果与深化应用。这主要体现在时间维度上的持续影响与空间维度上的全方位展现,其核心在于各参与主体在“后续发展期”内如何有效整合资源、促进互动合作。本研究聚焦于教学成果获奖后的建设与应用效果的持续深化问题,将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的“后续发展期”建设划分为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重构、资源的整合优化路径及外部保障体系的新建框架三个维度,旨在探讨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未来发展的理想形态与内在驱动力。
二、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后时代”建设动力机制分析
动力机制,即发展动力的来源与动力间的相互作用,是要素与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功能的整合。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后时代”建设动力机制指促进和推动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后时代”建设参与主体实施长期合作的推动力量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逻辑。职业院校、研究院所、行业企业、行政部门作为教学成果奖完整运行机制中四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承担着不同的职能。要构建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四个主要职能主体的“命运共同体”,必须把握“后时代”建设动力机制的整体性并关注系统的层次性与动态性,全面剖析其利益、资源、物质及能量相互影响与互动的机理与逻辑。
1.利益平衡机制
利益问题决定了职业教育改革参与主体如何参与育人过程及参与的程度与效果,是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后时代”建设动力机制中最根本的问题。

首先,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后时代”建设具有可持续发展动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参与主体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包括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和对人才资源建设降本增效要求两个方面。第一,向社会输送具有高效生产力的技术技能人才是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目标。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区域产业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了迫切需求,强化了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各职能主体参与“后时代”建设的意愿与行为。第二,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建设属于高投入高收益的育人活动,这也决定了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后时代”建设必然延续“校企合作”“校政合作”“校校合作”与“校企政合作”等建设模式。同时,成果培养的迟滞性与社会人才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也促使各主体主动参与人才培养,积极提升培养质量及效率。
其次,任何社会组织的存在都是由于其符合了一定利益群体的利益,实现了相关利益群体的期望。从教学成果“后时代”建设主体的职业院校的角度看,获奖教学成果的后续推广与应用能够为提高职业院校办学质量、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促进学生发展提供长效动力,且教学成果的后期稳固与落实是提高自身影响力与知名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从研究院所的角度来看,职业院校获奖教学成果的“后时代”建设为自身科学研究成果的产出提供了实践支撑,同时促使创新教育理论或理念的生成。从行业运行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的推广能够形成向企业特定职业岗位人才缺口的稳定输入链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企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从行政部门的角度来看,“促进公平,保障就业,改善民生”是其根本诉求,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应调节利益主体的内部关联性,各方兼顾,避免产生对原有“散”制度状态下形成的非正式约束的主体路径依赖,并形成稳定运行的利益闭环平衡机制。
2.资源整合机制
资源整合包括资源的持续流动和合理配置两个方面。资源的流动效率与配置效果是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改革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也是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后时代”建设运行机制中最活跃的因子,各构成要素在冲破原有体系后,会重新整合资源,形成一个协调互助、优势互补的可循环系统。从动力的逻辑发生点来看,资源流动的动力来源于主体之间所持有资源的持续性供给,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中各主体的持有资源及资源需求存在结构性差异,这种资源的异质性与多元性决定了成果“后时代”建设的可持续性。因此,明确职能主体的可供给资源是构建成果“后时代”建设主体互惠共生体系的首要环节。第一,职业院校的教育组织管理经验与能力、专家及骨干教师领导的优秀教师团队为教学成果“后时代”建设提供最坚实的物力及人力等基础性资源。第二,研究院所的专业科研与改革团队与职业院校之间形成成果的双向沟通与供给的链条。第三,根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根本要求,行业企业为成果“后时代”建设提供优质技术支持与信息平台支撑,实现教学成果与技术的深度融合。第四,政府部门应构建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后时代”建设的软环境,规定怎么做、由谁来做等相关任务归属。另外,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的资源配置效果体现在流动资源与主体需求间的匹配程度,必须形成资源流动与配置的二元整合机制,使“后时代”推广的各参与主体实现“有求必应”的建设生态。当下,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并未形成强制性、制度化的“后时代”建设体系,要为其发展提供长足发展的动力,必须秉持全场域资源共享的理念,打通各主体之间资源流动途径,形成教育资源、信息资源、文化资源的整合共生体系。
3.外部支撑与监管体系
在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的“后续发展期”建设中,外部支撑与监管体系构成了其运行机制的核心保障性要素,涵盖物质支持、制度框架及监督评价三大支柱。首要的是,坚实的物质支持体系是促成多利益主体间长期稳定合作的关键基石。加大对职业院校与科研机构在课程研发、实训基地构建、教育科研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并强化对企业在新兴技术革新、资源平台搭建上的扶持,能够构建一个自给自足的物质循环体系,为教学成果的“后续发展期”建设奠定稳固的物质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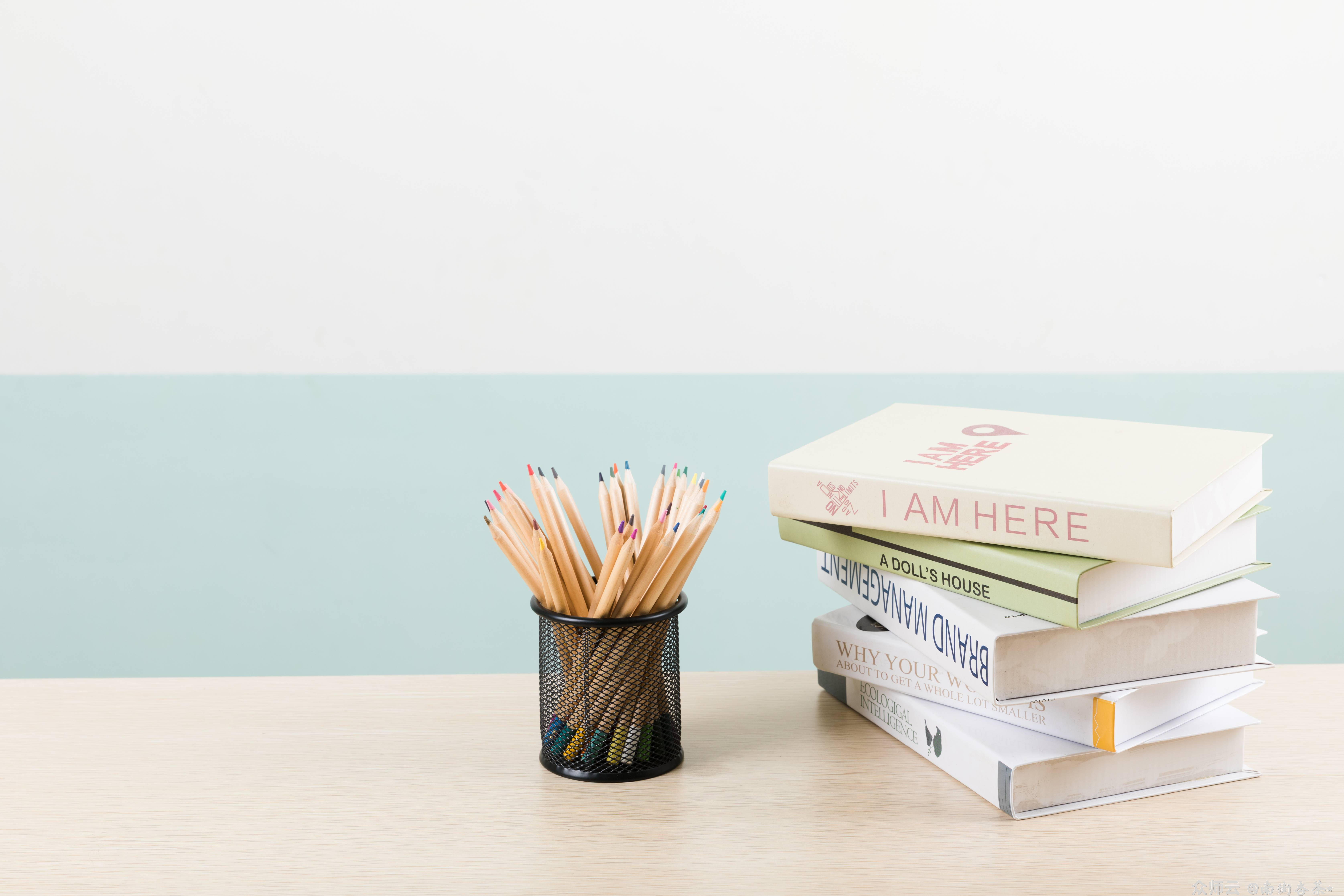
其次,基于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理论,个体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若缺乏明确且具体的制度约束,这种自利倾向可能导致市场秩序失衡,进而引发效率低下。鉴于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的“后续发展期”建设涉及多元主体的复杂教学改革实践,缺乏宏观政策的引导将使各主体在利益博弈中影响整体建设成效。此外,在人力资源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职业院校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而宏观政策的导向作用能有效规避“无序竞争”与“发展断层”。
最后,监督评价体系作为教学成果“后续发展期”建设的最后防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及第三方评审机构组成的评价组织,凭借其专业性、科学性和公正性,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进而推动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工作制度的革新。这一“他系统”不仅促进了教学成果的广泛传播,还通过定期的验收评估机制,为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的“后续发展期”建设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激励。